译文及注释
译文
暮春长安城处处柳絮飞舞、落红无数,寒食节东风吹拂着皇城中的柳树。
傍晚汉宫传送蜡烛赏赐王侯近臣,袅袅的轻烟飘散到天子宠臣的家中。
注释
春城:暮春时的长安城。
寒食:古代在清明节前两天的节日,禁火三天,只吃冷食,所以称寒食。御柳:御苑之柳,皇城中的柳树。
汉宫:这里指唐朝皇官。传蜡烛:寒食节普天下禁火,但权贵宠臣可得到皇帝恩的燃烛。《唐辇下岁时记》“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”。
五侯:汉成帝时封王皇后的五个兄弟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皆为候,受到特别的恩宠。这里泛指天子近幸之臣。
参考资料:
赏析
“春城无处不飞花,寒食东风御柳斜。”诗人立足高远,视野宽阔,全城景物,尽在望中。“春城”一语,高度凝炼而华美。“春”是自然节候,城是人间都邑,这两者的结合,呈现出无限美好的景观。“无处不飞花”,是诗人抓住的典型画面。春意浓郁,笼罩全城。诗人不说“处处飞花”,因为那只流于一般性的概括,而说是“无处不飞花”,这双重否定的句式极大加强了肯定的语气,有效地烘托出全城皆已沉浸于浓郁春意之中的盛况。诗人不说“无处不开花”,而说“无处不飞花”,除了“飞”字的动态强烈,有助于表现春天的勃然生机外,还说明了诗人在描写时序时措辞是何等精密。“飞花”,就是落花随风飞舞。这是典型的暮春景色。不说“落花”而说“飞花”,这是明写花而暗写风。一个“飞”字,蕴意深远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首诗能传诵千古,主要是其中的警句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,而这一句诗中最能耀人眼目者,就在一个“飞”字。
“寒食东风御柳斜”,春风吹遍全城,自然也吹入御苑。苑中垂柳也随风飘动起来了。风是无形无影的,它的存在,只能由花之飞,柳之斜来间接感知。照此说来,一个“斜”字也是间接地写风。
诗的前两句写的是白昼,后两句则是写夜晚:“日暮汉宫传蜡烛,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“日暮”就是傍晚。“汉宫”是借古讽今,实指唐朝的皇宫。“五侯”一般指东汉时,同日封侯的五个宦官。这里借汉喻唐,暗指中唐以来受皇帝宠幸、专权跋扈的宦官。这两句是说寒食节这天家家都不能生火点灯,但皇宫却例外,天还没黑,宫里就忙着分送蜡烛,除了皇宫,贵近宠臣也可得到这份恩典。诗中用“传”与“散”生动地画出了一幅夜晚走马传烛图,使人如见蜡烛之光,如闻轻烟之味。寒食禁火,是我国沿袭已久的习俗,但权贵大臣们却可以破例地点蜡烛。诗人对这种腐败的政治现象做出委婉的讽刺。
这首诗善于选取典型的题材,引用贴切的典故对宦官得宠专权的腐败现象进行讽刺。虽然写得很含蓄,但有了历史典故的暗示,和中唐社会情况的印证,读者还是能了解诗的主题的。
参考资料:
赏析二
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的节日,在清明前两天,是从春秋时传下来的,是晋文公为了怀念抱木焚死的介子推而定的。
据孟棨《本事诗》记载:德宗时制诰缺乏人才,中书省提名请求御批,德宗批复说:“与韩翃”,当时有两个韩翃,于是中书省又以两人的名字同时进呈。
德宗便批与写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的韩翃。这虽是一段佳话,但足见《寒食》这首诗的广泛流传和受到的赏识。
这是一首讽刺诗,但诗人的笔法巧妙含蓄。从表面上看,似乎只是描绘了一幅寒食节长安城内富于浓郁情味的风俗画。实际上,透过字里行间可感受到作者怀着强烈的不满,对当时权势显赫、作威作福的宦官进行了深刻的讽刺。中唐以后,几任昏君都宠幸宦官,以致他们的权势很大,败坏朝政,排斥朝官,正直人士对此都极为愤慨。本诗正是因此而发。
“春城无处不飞花,寒食东风御柳斜”,这两句描写春日长安城花开柳拂的景色。“无处”指花开既多又广、“飞花”写花开的盛况,时值春日,长安城到处是飞花柳絮,一派缤纷绚烂的景象。“东风”指春风,“御柳斜”是状摹宫苑杨柳在春风吹拂下的摇摆姿态。“斜”字用得妙,生动地写出了柳枝的摇曳之神。这是寒食节京城的白天景色。景色由大而小,由全城而入宫苑。下面接着写宫苑傍晚的景象。“日暮汉宫传蜡烛,轻烟散入五侯家”,是写天黑时分,宫苑里传送着一支支由皇帝恩赐给宦官的蜡烛。蜡烛燃烧通明,升腾起淡淡的烟雾,袅袅娜娜地萦绕在宦官家,到处弥漫着威福恩加的气势!使人如见他们那种炙手可热、得意洋洋的骄横神态。在封建习俗的统治下,不要说全城百姓,就连那些不是宠臣的朝官之家,在禁止烟火的寒食之夜,恐怕也都是漆黑一片。
唯独这些宦官之家,烛火通明,烟雾缭绕。由一斑而见全豹,仅此一点,足见这些宦官平日如何弄权倚势,欺压贤良。作者在这里仅用两句诗,写了一件传蜡烛的事情,就对皇帝的厚待亲信宦官,宦官的可恶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,达到了辛辣讽刺的目的。
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,原作者已无法考证。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,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。
创作背景
唐代制度,到清明这天,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。这仪式用意有二:一是标志着寒食节已结束,可以用火了;二是藉此给臣子官吏们提个醒,让大家向有功也不受禄的介子推学习。中唐以后,几任昏君都宠幸宦官,以致他们的权势很大,败坏朝政,排斥朝官。有意见认为此诗正是因此而发。
参考资料:
韩翃,唐代诗人。字君平,南阳(今河南南阳)人。是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。天宝13年(754)考中进士,宝应年间在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府中任从事,后随侯希逸回朝,闲居长安十年。建中年间,因作《寒食》诗被唐德宗所赏识,因而被提拔为中书舍人。韩翃诗笔法轻巧,写景别致,在当时传诵很广。
《毛诗序》选段
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言之不足故嗟叹之,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,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
《典论·论文》选段
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讬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
《诗品序》选段
若乃春风春鸟,秋月秋蝉,夏云暑雨,冬月祁寒,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,离群讬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,汉妾辞宫。或骨横朔野,魂逐飞蓬。或负戈外戍,杀气雄边。塞客衣单,孀闺泪尽。或士有解佩出朝,一去忘返。女有扬蛾入宠,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,感荡心灵,非陈诗何以展其义?非长歌何以骋其情?故曰:“诗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,幽居靡闷,莫尚于诗矣。
《与元九书》 选段
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,莫始乎言,莫切乎声,莫深乎义。诗者:根情,苗言,华声,实义。
《题画》画竹题记一则
江馆清秋,晨起看竹,烟光日影露气,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。胸中勃勃遂有画意。其实胸中之竹,并不是眼中之竹也。因而磨墨展纸,落笔倏作变相,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总之,意在笔先者,定则也;趣在法外者,化机也。独画云乎哉!
《人间词话》三则
词以境界为最上,有境界则自成高格,自有名句。
境非独谓景物也,喜怒哀乐,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,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回头蓦见,那人正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,恐为晏、欧诸公所不许也。
曼卿讳延年,姓石氏,其上世为幽州人。幽州入于契丹,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闲走南归。天子嘉其来,将禄之,不可,乃家于宋州之宋城。父讳补之,官至太常博士。
幽燕俗劲武,而曼卿少亦以气自豪。读书不治章句,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,视世俗屑屑无足动其意者。自顾不合于时,乃一混以酒然好剧饮大醉,颓然自放。由是益与时不合。而人之从其游者,皆知爱曼卿落落可奇,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。年四十八,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卒于京师。
曼卿少举进士,不中,真宗推恩,三举进士皆补奉职。曼卿初不肯就,张文节公素奇之,谓曰:“母老乃择禄耶?”曼卿矍然起就之,迁殿直。久之,改太常寺太祝,知济州金乡县。叹曰:“此亦可以为政也。”县有治声,通判乾宁军。丁母永安县君李氏忧,服除,通判永静军。皆有能名。充馆阁校勘,累迁大理寺丞,通判海州。还为校理。
庄献明肃太后临朝,曼卿上书,请还政天子。其后太后崩,范讽以言见幸,引尝言太后事者,遽得显官,欲引曼卿,曼卿固止之,乃已。
自契丹通中国,德明尽有河南而臣属,遂务休兵养息,天下晏然内外驰武三十余年。曼卿上书言十事,不报,已而元昊反,西方用兵始思其言,召见。稍用其说,籍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之民,得乡兵数十万曼卿奉使籍兵河东,还称旨,赐绯衣银鱼。天子方思尽其才,而且病矣既而闻边将有欲以乡兵扦贼者,笑曰:“此得吾粗也。夫不教之兵,勇怯相杂,若怯者见敌而动,则勇者亦牵而溃矣。今或不暇教,不若募其教行者,则人人皆胜兵也。”
其视世事,蔑若不足为。及听其施设之方,虽精思深虑,不能过也状貌伟然,喜酒自豪,若不可绳以法度。退而质其平生趣舍大节,无一悖于理者。遇人无贤愚,皆尽忻,及闲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恶,当其意者无几人。其为文章,劲健称其意气。
有子济、滋。天子闻其丧,官其一子,使禄其家。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茔,其友欧阳修表于其墓曰:
呜呼曼卿!宁自混以为高,不少屈以合世,可谓自重之士矣。士之所负者愈大,则其自顾也愈重,自顾愈重,则其合愈难。然欲与共大事,立奇功,非得难合自重之士,不可为也。古之魁雄之人,未始不负高世之志,故宁或毁身污迹,卒困于无闻。或老且死,而幸一遇,犹克少施于世。若曼卿者,非徒与世难合,而不克所施,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寿,其命也夫!其可哀也夫!
春光还是旧春光。桃花香。李花香。浅白深红,一一斗新妆。惆怅惜花人不见,歌一阕,泪千行。
楼外绿阴深,凭栏指点偏东。
浑河水、一线如虹。
清凉极,满谷幽禽啼啸,冷雾溟濛。
任海天寥阔,飞跃此身中。
云容。
看白云苍狗,无心者、变化虚空。
细草络危岩,岩花秀媚日承红。
清风阁,高凌霄汉,列岫如童。
待何年归去,谈笑各争雄。
 韩翃
韩翃 白居易
白居易 佚名
佚名 欧阳修
欧阳修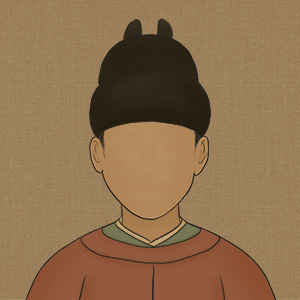 和凝
和凝 秦观
秦观 顾太清
顾太清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曾原郕
曾原郕 王炎
王炎 石孝友
石孝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