忆昔行
忆昔当年十四五,尝看秋潮到江浒。飞裾径上酒家楼,凭栏直望潮生处。
数百里间名海门,悠悠一线色如银。渐近江心痕渐大,汹涌声吞十万军。
须臾潮头高数丈,众潮随接皆奔上。中有雄心拍浪儿,几点红旗争荡漾。
风前缥缈夺标来,神蛟鬼鳄俱摧颓。监潮侯有伍胥在,但见濆薄旋推回。
后来沙涨西兴口,潮势何曾十分有。水上人骑骒马行,车如鸡栖马如狗。
数年之后不可当,漰湃惊闻洗目塘。汪洋且拨菜园去,坝子桥边亦渺茫。
神皋内史承天旨,摆桩叠石曾料理。至今遏捺逾十年,桩石如城牢在水。
江头人谓可安居,连年不奈还忧虞。西风吹潮半夜起,子胥之怒知何如。
阴威作寒带烟雾,捲石掀沙出幽府。堪羡云中拍浪儿,踏著危机不怕危。
乘除消长君休忽,牢执长竿一面旗。
秋水时至,百川灌河。泾流之大,两涘渚崖之间,不辩牛马。 于是焉,河伯欣然自喜,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顺流而东行,至于北海。东面而视,不见水端。于是焉,河伯始旋其面目,望洋向若而叹曰:“野语有之曰:‘闻道百,以为莫己若’者,我之谓也。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,而轻伯夷之义者,始吾弗信,今吾睹子之难穷也,吾非至于子之门,则殆矣,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。”
北海若曰:“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,拘于虚也;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,笃于时也;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,束于教也。今尔出于崖涘,观于大海,乃知尔丑,尔将可与语大理矣。天下之水,莫大于海。万川归之,不知何时止而不盈;尾闾泄之,不知何时已而不虚;春秋不变,水旱不知。此其过江河之流,不可为量数。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,自以比形于天地,而受气于阴阳,吾在天地之间,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方存乎见少,又奚以自多!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,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?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?号物之数谓之万,人处一焉;人卒九州,谷食之所生,舟车之所通,人处一焉。此其比万物也,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?五帝之所连,三王之所争,仁人之所忧,任士之所劳,尽此矣!伯夷辞之以为名,仲尼语之以为博。此其自多也,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?”
冷落词赋客,萧索水云乡。援毫授简,风流犹忆东梁。望虚檐徐转,回廊未扫,夜长莫惜空酒觞。
 李龏
李龏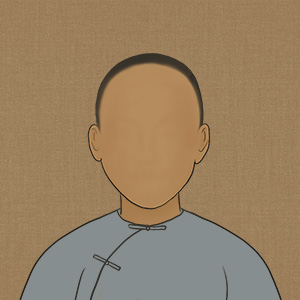 庄子及门徒
庄子及门徒 诸葛亮
诸葛亮 刘墉
刘墉 段成己
段成己 牛希济
牛希济 毛泽东
毛泽东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周邦彦
周邦彦 刘镇
刘镇